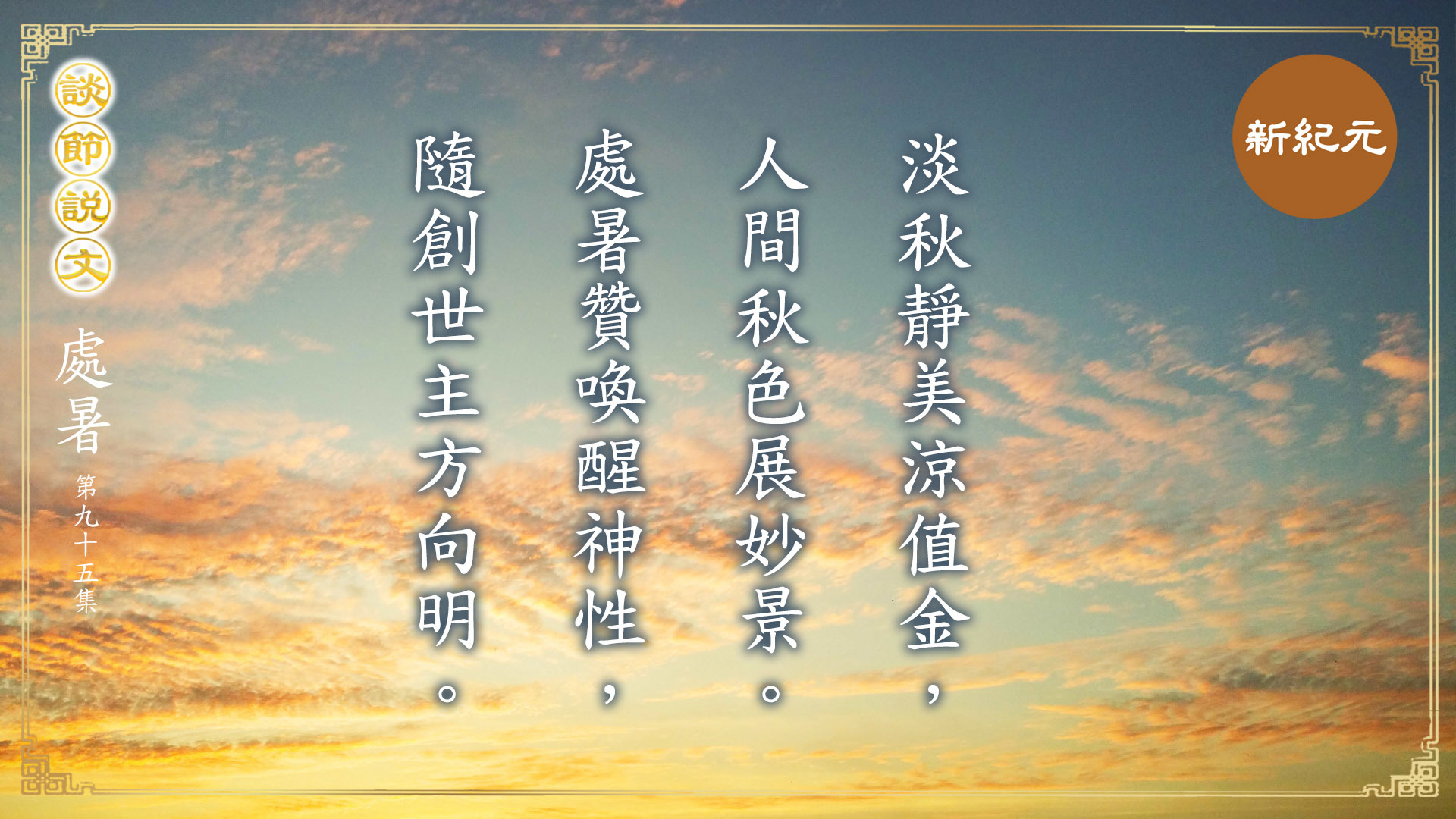許那和于宙 用生命譜寫震撼旋律

北京畫家許那(右)和丈夫于宙。(明慧網)
去年「7.20」前夕,北京畫家、詩人、法輪功學員許那再次遭綁架,至今身陷囹圄。值此「7.20」法輪功遭受不白之冤、承受莫名苦難的第22個年頭,本文以許那和于宙夫婦生離死別的故事為縮影,一窺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最慘烈、最悲壯,也最感人、最輝煌的一段正在你我身邊發生的歷史。
文:文華
(訂閱 新紀元Youmaker)
人都有個本能,不自覺中就會選擇遠離痛苦,所以在酷刑折磨下,很多人會屈打成招,這是完全可以理解並值得同情的。然而就在當今中共監獄裡,卻有一群人,他們好像是特殊材料煉就成的,能承受一般人無法承受的痛苦,在超越生死、在生命昇華中,閃閃發光。其中包括北京一對藝術家夫婦。
許那的丈夫叫于宙,他們生活在北京這個被稱為中國最文明的城市,而他們遭遇的卻是最不文明的酷刑:許那三次被關進大牢,原因都是法律無法解釋的。
第一次是2001年,她把自己的住房借給朋友居住而被判刑五年;第二次是2008年,她車裡有一本書而被判刑三年;第三次是2020年她在家裡和朋友們一起讀書被抓,目前已被關押11個月,正在等待法庭判決。
許那出生美術世家
許那1968年出生於吉林長春,父親是文聯畫家,母親生前是吉林美院老師。夫婦倆為人忠厚,注重品行修養。為了讓女兒時刻記住要少說多做,就取《論語.里仁》中的「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給女兒取名「許訥」。
由於文革時,中共破壞了傳統文化,很多人常把「訥」字讀錯,於是她把名字改成了「許那」。
1987年高考時,她的成績遠遠超過北京大學的錄取分數線,但由於她不是團員,政審不合格,而沒被北大錄取,只讀了北京廣播學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國傳媒大學。
1989年天安門屠殺之前,她和同學們上街遊行,打出「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標語。「六四」後,她不願意成為「黨的喉舌」,改行成了畫家。

許那生活照。(明慧網)
畫如其人 具有詩意
由於中共封鎖,目前在大陸網站上看不到她的作品介紹,不過在業內,許那卻小有名氣:1997年她的得獎作品參加了文化部的中國藝術大展;1998年她在中國青年油畫展中又獲嘉獎。

許那的獲獎證書。(明慧網)
那時,許那的畫在香港也很有名,一張油畫的售價達到幾萬元。美術界的行家評論說,她的畫筆法純熟,色彩質樸。從畫中淡雅的野花、青青的原野和寧靜燈光下的書桌中,能夠感受到作者心中的那份美好和平靜。
畫如其人,那時候,許那已經修煉法輪功兩、三年了。那畫中的祥和寧靜正是許那修煉後淡泊心境的體現。
于宙通曉多語種 愛音樂
于宙是許那的東北老鄉,長得魁梧,一米八幾的大個子,讓一米六二的許那顯得很小巧。
朋友們都說于宙是個「大才子」,他畢業於北京大學法語系,通曉多種語言,不過他更喜歡音樂,精通吉他、打擊樂和口琴,歌唱得也不錯。

畢業於北京大學法語系,于宙通曉多種語言,不過他更喜歡音樂,精通吉他、打擊樂和口琴,歌唱得也不錯。(明慧網)
儘管多才多藝的于宙在日常生活中像個哲學家,平日不苟言笑,可絕對幽默。朋友們都說他不說話則已,一說話準能把你逗得樂一個跟頭。
于宙很有藝術天賦,對詩詞歌賦也很有研究,當時在年輕人的藝術圈子裡小有名氣。同樣多才多藝的許那,夫唱婦隨,琴瑟相合,生活很美滿。
1995年,于宙從朋友那聽說法輪功,他想學,許那也想學,夫妻倆都覺得以「真、善、忍」為原則的法輪大法真是太好了,教人做好人,同時還能提高自己。為了探詢人生真諦,他們雙雙走上了法輪大法的修煉之路。
善良的修煉人故事
說起于宙夫妻,朋友們都說「他們兩口子實在是太善良了」、「只能用善良來形容,找不著別的合適的詞兒」。

說起于宙和許那夫妻,朋友們都說只能用善良來形容,找不著別的合適的詞。(明慧網)
開始修煉後,他們覺得大法很好,就時常向朋友們介紹,希望能讓更多的人從修煉中受益。于宙還曾經義務參與過法文版《轉法輪》的翻譯工作。
于宙對遇到的每一個人都一樣的好,比如有一次家裡來了個並不熟識的人,向他訴說自己有多困難,于宙兩口子為了幫助這個人,一下就從自己這個月僅有的1000多元裡拿出800多元,只給自己留了一點吃飯錢。
北京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藝人,人稱「北漂一族」,大家都希望將來能在演藝界有所成就,但是在娛樂圈裡混很不容易,有的生活很艱苦。于宙夫妻倆就經常幫助這些同行,比如把自己曾租住的房子免費給這些朋友們住,還常常在經濟上給他們一些幫助。
于宙對人很寬容,有一次一位朋友跟于宙約好在車站見面,晚了一個多小時,到了地方一看,于宙還一直在那等他。兩個人見面,于宙連一句為什麼晚了都沒問,只說了一句「咱們走吧」,就去辦該辦的事,事後也從不提起,直到今天,那位朋友講起這件事情還覺得很感動。
有一次于宙開車和朋友出去辦事,看見路當中有塊大石頭,其他車輛都繞著石頭走,搞得路很堵。于宙把車停在石頭前,自己把那塊石頭搬開,然後繼續趕路。朋友們都讚歎,這年月還有這樣的人?
1998年,于宙和小娟、黎強,組成了三人民謠樂團,叫「小娟&山谷中的居民」(Valley Children)。小娟三歲開始唱歌,是位民謠創作人,儘管她身有殘疾,但她對生活給予的一切,都回報一份質樸的愛。黎強是吉他手,他和小娟是夫婦。于宙擔任口琴、長笛以及打擊樂手。他們用各種語言演唱民謠,為人帶來安詳與幸福之美。

1998年,于宙(左)與黎強、小娟夫婦組建了民謠樂隊,叫「小娟&山谷中的居民」。(大紀元)
無辜被判刑五年
法輪功,又叫做法輪大法,是源於中國古老傳統的佛家修煉大法。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從中國東北的長春市傳出。法輪功要求修煉者嚴格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有五套簡單易學的功法。因袪病健身、淨化身心有奇效,法輪功迅速傳遍全中國,傳到全世界。

法輪功於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從中國長春市傳出,要求修煉者嚴格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有五套簡單易學的功法。圖為2019年5月18日5000名法輪功學員在紐約總督島排字,慶祝世界法輪大法日。(新唐人)
憑藉人傳人、心傳心,法輪功已傳播到亞、歐、美、澳、非五大洲的110多個國家和地區。北到北極圈內的芬蘭羅瓦涅米市,南到靠近南極的紐西蘭南島,東到太平洋上的塞班島,西到大洋西岸邊的紐約長島,到處都有法輪功學員的身影。
然而,獨裁中共卻容不下這群修煉做好人的人,因為他們相信神佛的存在,相信在人之上還有更高級的生命。
儘管當時北京有醫學單位調查顯示,修煉法輪功之後,人們身體得到好轉或疾病康復的,即煉功有效率的,達到98%以上,這為國家節約了大量醫療費,同時隨著道德提升,對社會精神文明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本來這些的最大受益者是當權的中共,然而當時的中共黨魁江澤民是踩著「六四」鮮血上位的,出於一己的妒忌和玩弄權術,江澤民想藉鎮壓修煉人來給自己樹立權威,於是他不顧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反對,一意孤行開始瘋狂鎮壓法輪功,提出要在三個月內消滅法輪功。
面對無端的誣陷和打壓,全國各地的法輪功學員紛紛自發地到北京上訪,想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讓中共高層能真實地了解法輪功。
1999年7月20日中共打壓開始後,據中共內部消息,法輪功進京上訪以2000年初到2001年底最多,北京公安局根據新增的饅頭消耗量,估算當時到北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在高峰期超過100萬人。

2000年12月天安門廣場,便衣奔向祥和舉著法輪功橫幅的善良老人、青年和孩子。(明慧網)
那時很多法輪功學員省吃儉用,一日三餐就吃饅頭和鹹菜,只是為了能更長時間留在北京,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來的人中不少是東北老鄉,于宙、許那夫婦看到他們生活很困難,就常常在家裡接待外地功友們,為他們提供臨時的食宿。
2001年,借住在許那家的東北四平法輪功學員李小麗(已被迫害致死)被抓,警察根據李小麗的電話號碼查到了許那另外租住的地方,7月3日北京市國安在通州綁架了許那,11月北京房山中級法院對許那非法判刑五年。
她硬是挺過來了
北京女子監獄裡條件很殘酷,尤其是對法輪功學員。為了所謂的「轉化」,監獄最常用的一種酷刑就是「熬鷹」,漁民就是用這種方法來強制訓練魚鷹聽話,因為不讓睡覺,無論是對動物還是人類,都會帶來難以承受的精神上和肉體上的痛苦,魚鷹因為怕被熬鷹,被訓練得每天把從水中叼上來的魚都交給漁夫。
警察每天只讓許那睡四個小時,白天還要幹重體力活兒。為了為難她,許那進監獄的第一天就給她分配了普通犯人訓練一年後才能完成的工作:一天做600雙拖鞋的鞋幫子。
從小養尊處優的許那,從沒幹過這種苦活,但她憑藉一個修煉人堅強的意志力,硬是挺了下來!
2002年11月,許那被轉到北京女子監獄三監區,在這裡,許那被完全剝奪了睡眠,還把她的腿捆綁起來、強迫雙盤很長時間、在雪地裡凍、一個多月不讓她洗漱等。

2002年11月,許那被轉到北京女子監獄三監區,被完全剝奪了睡眠,還把她的腿捆綁起來、強迫雙盤很長時間、在雪地裡凍、一個多月不讓她洗漱等。部分酷刑示意圖。(明慧網)
憑藉堅定的信仰,許那還是挺了過來,沒有放棄修煉。
善感化著周圍人
令人震驚的是,儘管她在監獄裡處處遭遇折磨和不幸,但是許那卻對每個人都一樣好,包括那些被派來用酷刑折磨她的警察,還有時刻監視她的包夾犯人。
在勞累忙碌之餘,許那給那些派來包夾她的刑事犯畫肖像,給每個人講述法輪大法的美好和自己修煉的感受。漸漸的,很多警察和犯人都被法輪大法的美好,和大法修煉者的善良所感動,紛紛私下裡想辦法幫助法輪功學員,甚至很多人也學煉了法輪功。
許那心靈手巧,加上她的藝術功底,她做的手工藝品不但很精緻,而且富有藝術價值。監區長田鳳清逼迫許那的家人提供所需一切材料、費用,讓許那製作手工藝作品,賣給在押人員和來探親的家屬,因為那些東西實在很精緻可愛,所以總有人買。其他警察看著眼紅,就把田鳳清給告了。
監獄的生活條件十分艱苦,伙食很差,用犯人們的話說,「吃得不如豬狗,睡得不如牛羊」。為了補充點營養,不少犯人從監獄開的高價商店中買一些食品,這叫「採買」。
為了讓許那轉化,監獄剝奪了她「採買」的權利。難友們沖方便麵吃的時候,經常會背著警察分給許那一半。許那知道在這個艱苦的環境下,這些方便麵來之不易,也理解難友們的深深的情意。她每次都挑起一兩根來,一邊誇讚著好吃,一邊把麵條推還給同樣也是面黃肌瘦的獄友們。
北京女子監獄常常給許那調換監區和牢房,不久警察們發現許那有改變環境的能力,她能夠讓所有和她相處的人都變好,這令中共惡警的頭子們很驚愕。
每次許那被調離一個監區,原來監區的犯人們都捨不得許那,為她灑淚送別。每次當許那調到新的監區後,就有更多的人被許那的善心感化。
為死去功友吶喊
許那堅持真理,盡一切可能為自己和其他難友爭取正當的權利。在一次列隊集合時,監獄長經過,許那出其不意地從隊列中跑出,攔住了監獄長,當面反映自己所受的種種摧殘,要求停止迫害,給她一個合理的說法。
2002年底,監獄長看始終不能轉化許那,許那反而影響了這麼多人,決定把許那關押進單間,盡量使她不能接觸其他人。就是在這裡,許那親眼看到了一幕恐怖的人間慘劇。
監獄的這些「單間」裡關押的都是堅持信念的法輪功學員,她們經常被警察派來的刑事犯人暴力毆打。其中有一個叫董翠芳,被關在許那的隔壁。
董翠芳是醫學研究生,北京順義區婦幼保健醫院的醫生,才29歲。2003年3月11日上午被轉到北京女子監獄三分監區。一天許那聽到隔壁董翠芳的呻吟和她被打的聲音。許那趁包夾人不注意,就衝到董翠芳的房間對打手喝到:「不許打人!」包夾許那的人馬上跑來強行拽走許那。
3月18日,監獄分區長田鳳清將整治董翠芳的任務交給了惡警習學會,安排其到浴室教訓董翠芳。習學會、董曉慶(原三分監區惡警)帶領曾經煉過法輪功,後來被洗腦轉化的李小兵、李小妹等五人,將董翠芳帶到樓下鍋爐房旁邊的平房浴室內,之後慘劇發生了。幾個小時以後,許那在窗戶邊親眼看到被活活打死的董翠芳被人抬走了!

2003年3月18日,堅持信念的北京順義區婦幼保健醫院醫生,年僅29歲法輪功學員董翠芳被活活打死。(明慧網)
這事卻被監獄隱瞞起來了。一天,許那和大家一起吃午飯,看到大夥兒都在,她對李小妹說:「你是殺人犯!你們把董翠芳打死了!」大家都吃了一驚,李小妹嚇壞了,把飯桌都掀了,拉著許那找獄警。
不久北京SARS流行,許那給監獄長寫信,在信中提及董翠芳的死,講善惡有報的道理,希望監獄長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停止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這封信把監獄長嚇得夠嗆。董翠芳的死是他的心病,他就怕別人知道。所以許那馬上被隔離,再次被關進了「小號」(禁閉室),許那不得不絕食抗爭,並長期被灌食。

因檢舉、控告董翠芳被虐死的事實,許那再次被投入小號折磨,並長期被灌食。示意圖。(明慧網)
被關小號和灌食
關小號是一種殘酷的酷刑,人被關在一個小小的房子裡,頭頂上是強烈刺激人的燈光,周圍沒有一個人,只有孤零零的一個人在痛苦中煎熬。
據法輪功學員周向陽回憶他在天津市港北監獄關小號並同時被「地錨」酷刑折磨的經歷:「小號長三米,寬一米,高約一米六,沒有窗戶,陰暗潮濕,密不透光。屋頂上掛一燈,24小時亮著,地上一側二米長的地方鋪著高約二、三十厘米的木板。我被仰躺在木板上面,兩個胳膊成V字形向外張開(屋寬一米,手臂不能伸直),手反銬在地環上,膝蓋以下小腿部位和腳懸在水泥地上,墜著腳鐐,腳鐐是鎖在地上的,手銬和腳鐐沒有任何活動的餘地。」
中共監獄中的灌食,並不是為了防止絕食人員出現生命危險而採取的醫療手段,而是另一種酷刑。
據明慧網2010年不完全統計,暴力灌食直接導致死亡的中國法輪功學員,有名有姓的就至少有358例。
在中共監獄裡,警察給法輪功學員灌的食物還包括濃鹽水、濃辣椒水、大蒜汁、芥末油、人尿、大糞水、高濃度酒,甚至摧毀神經系統的不明藥物。
強制灌食一般分為撬嘴直接灌食和鼻飼灌食兩種。灌食時,警察故意叫人來回抽拉灌食的管子,使受害者遭受慘烈劇痛;有時管子插到氣管、肺部,造成有的法輪功學員在被灌食過程中當場死亡。
幸運的是,許那活下來了。
「每一個被扭緊的螺絲釘都是有罪的」
在經歷五年的酷刑折磨後,2006年許那回到家中,並寫下這樣一篇回憶:

在經歷五年的酷刑折磨後,2006年許那回到家中,寫下一篇回憶:那些自以為自己在中國自由的人,他們不知道自己生活於一個無形的大監獄中。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你認同它存在。每一個被扭緊的螺絲釘都是有罪的,它加固了這個機器的邪惡運轉。(明慧網)
一、我多麼希望自己被關押的是奧斯維辛集中營,而不是中國的監獄。因為在納粹的毒氣室,人可以迅速死亡;而在北京女子監獄,它讓你活著生不如死。反覆經歷漫長的酷刑,酷刑中他們配備懂醫的犯人看護,隨時檢測你的體徵。我在那兒多日不被允許睡覺,被發現心律不齊。於是警察命令說:「讓她睡一小時,休息一下。」
各種各樣隱蔽而精緻的酷刑被發明,比如劈叉,將雙腿拉開成180度,命令三個犯人坐在受刑人的雙腿及後背上,反覆按壓。警察自豪於這個發明:「這個辦法好,因為疼痛難忍,但又不傷及骨頭。」
納粹反人類的目的是消滅猶太人的身體,而它們的目的是摧毀人的精神、良知。當我在酷刑與洗腦中更加挺直腰板時,一個警察認真地對我說:「應該申請對你進行開顱手術,把你的大腦摘掉。」
那些自以為自己在中國自由的人,他們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摘除了精神,生活於一個無形的大監獄中。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你認同它存在、認同它應該繼續存在,獲罪於天,豈能長久?
所以每一個被扭緊的螺絲釘都是有罪的,它加固了這個機器的邪惡運轉。那些想從它那裡得到名利和各種好處的,正如孔子所說:「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
二、我受到傳媒的最深刻的教育,不是在大學課堂,而是在監獄。2003年電視臺的節目主持人徐滔採訪北京女子監獄,我被隔離在警察辦公室。四個犯人,以人肉銬子的形式箝住我,我可以清晰聽到不遠處採訪現場,對我施予酷刑的警察和犯人在宣講它們如何文明執法,而我不能發出一點聲音,我的嘴裡被堵上了毛巾。
徐滔是我大學同學,我們共同受教於以培養黨的喉舌為宗旨的中國傳媒大學,如今她是北京電視臺的副總編輯、全國人大代表。
這次採訪後不久,一名法輪功修煉者董翠芳被活活虐死在女監。最後稱她為病死,我因檢舉、控告她被虐死的事實,再次被投入小號折磨。
幾年後,同樣被「病死」的是我的丈夫于宙。與他同一監室的在押人員承認,他為于宙的死做了偽證,但他說:「我不敢講出全部,我害怕被警察滅口。」
我的好朋友孫毅,因為從馬三家勞教所成功寄出一封求救信,講述了他被奴役迫害的事實,最後即使他到了印尼的一個小島,也沒躲過它伸長的手。

孫毅從馬三家勞教所寄出一封求救信講述他被迫害的事實,最後即使到了印尼的一個小島也沒躲過中共伸長的手,2017年10月1日在印尼巴里島的醫院突然離世。圖為紀錄片《求救信》海報。(Joyce 提供)
三十多年前,我因政審不合格,不是團員,儘管分數遠遠超過北大的錄取分數線,也被拒收,誤入傳媒大學。
89學潮時,我和我的同學上街遊行,共同打出過「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標語。
「六四」以後,我決心遠離它,離開廣電部改行成為一個自由畫家,對世事不聞不問,以為從此可以歲月靜好。
多年的親身經歷使我覺醒,這個國家的每一件不公義都離我很近,我不能裝作看不見,它最後真的發生在我的身上。這個世界每一件不公義,即使離你很遠,也與你息息相關,因為他時刻拷問著你的良知。
有些事於我不僅是權利,也是責任,我無可逃避。
于宙離奇死亡 醫生不敢屍檢
許那回家後,夫婦團圓,對于宙和許那的事業都有很大的促進。
2007年于宙所在的「小娟和山谷裡的居民」和著名音樂頻道Channel簽約,他們的樂隊被譽為2007年不能錯過的民謠組合,他們的歌聲被稱為「2007年最溫暖的聲音」。
許那也被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免試錄取為研究生,並在2007年以優秀作品獎入選首屆中國青年百人油畫展。
然而好景不常,很快隨著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中共的魔爪再次施加在這對夫婦身上。
2008年1月26日晚10點左右,于宙演出結束後,與妻子開車回家,行駛到通州北苑的楊莊路段被警察攔截,進行「奧運搜查」。因為發現車上有《轉法輪》這本法輪功學員經常讀的書,警察就將他們抓到通州區看守所。
第二天,許那的父母和妹妹家,都被警察抄家。
2月6日大年三十,被通州看守所關押10天後,年僅42歲、身體健康的于宙突然死亡。

于宙因修煉法輪功,2008年1月26日晚在回家路上被攔截,2008年2月6日,被通州看守所關押10天後,年僅42歲、身體健康的他突然死亡。(明慧網)
警察一會謊稱是絕食身亡、一會又謊稱是糖尿病導致死亡,家人強烈做屍檢,但醫生拒絕了,他們不敢做,所以于宙的遺體至今停發在清河急救中心。
醫院要求火化,家屬就要求警察把許那從看守所放出來,主持丈夫的喪禮,但中共警察卻殘酷地拒絕了這個要求,令許那無法與丈夫見上最後一面。
他們還把許那關押到北京市公安局市局七處,那裡是專門關押政治犯和重型刑事犯的地方,文革中曾經處死過遇羅克,文革後迫害過魏京生,現在那裡又關押著眾多堅守信仰的法輪功學員。
美麗的魂魄 優秀的音樂人
2008年2月7日,是中國新年的大年初一。小娟本來應該感到快樂的,她主唱的《我的家》MV唱片已經進入了最後的製作,這是「小娟&山谷中的居民」這個三人的民謠樂隊第一個MV。但這天,小娟在她的個人博客上發表了她創作於十多年前的無伴奏清唱《美麗的魂魄》:
「隨著時光的流逝 我們會變成美麗的魂魄飄在遙遠的天空
也許是你先也許是我先 折一朵天堂聖潔的玫瑰在天堂靜靜地等候」
在這個萬家歡樂的日子,小娟憂鬱傷感但磁性的歌聲並不應景,這是她為老朋友于宙在送行。據于宙的朋友們回憶,于宙在樂隊裡是鼓手,同時也吹口琴。他打鼓很有創新,是把非洲的手鼓和西洋的打擊樂的鼓韻結合起來。而且他在那方寸之地準備了很多各種各樣的小東西,能模擬出各種各樣自然的聲音。
不少歌迷反饋說,聽他們的歌,真的像他們說是山谷裡的居民,是在山谷裡唱的,能感受到那種山谷的清新。
他們主要作品〈紅布綠花朵〉,還有〈我的家〉、〈晚霞〉等,都非常受歡迎。
于宙也會唱歌,他常給歌迷唱的是〈愛的箴言〉。他唱歌的時候,很多人感覺他是流著眼淚在唱,底下聽眾也是流著眼淚在聽。
歌中唱到:
「我將真心付給了你 將悲傷留給我自己
我將青春付給了你 將歲月留給我自己
我將生命付給了你 將孤獨留給我自己
⋯⋯
愛是沒有人能了解的東西
愛是永恆的旋律
愛是歡笑淚珠飄落的過程
愛曾經是我也是你」
于宙顯靈 呼籲營救許那
這首歌也許能反映出于宙和許那彼此深厚的愛情。等他去世後,于宙的家人經歷了一件神奇的事。
于宙在2008年黃曆新年除夕被迫害致死,他的親人十分悲痛,由於受中共無神論的洗腦教育,家人們原本不相信神的存在。
可是就在許那被非法審判期間,于宙的親人反覆連續做同樣的夢:一匹潔白的天馬從天而降(于宙屬馬),身上放射著耀眼的光焰,在空中奔跑著來到親人的身邊,變化成于宙生前的形象,笑呵呵的告訴親人,自己現在在南邊天上一個像廟宇那樣的建築群的地方等候著,那裡沒有人世的苦,一切都很美好,同時希望自己的親人們能幫助許那。
類似的夢反反覆覆的出現,真實而且清晰,用現代科學根本解釋不通,于宙的親人終於對神的存在深信不疑。
他們開始積極協助許那的父母,並通過他們在比利時和德國的朋友、親人,其中包括德國的官員們,呼籲釋放許那。
然而中共一意孤行。2008年11月25日,許那被非法審判,開庭時間近幾分鐘,為許那寫了無罪辯護詞的辯護律師也沒有能夠出庭,豐臺區法院的法官甚至沒有讀宣判書,就把「有期徒刑三年」的結果宣布了。
三年的獄中苦難依舊是罄竹難書,等到2011年許那出獄後,警察依舊經常騷擾她,許那也依舊堅如磐石地修煉法輪功。
第三次被抓 為良知戰鬥
2020年7月19日,許那被北京順義區空港派出所所長帶著國保警察從家中被綁架走。7月20日,警察再次登門,非法抄家,抄走所有電子產品和攝像機。
7月24日,北京律師梁小軍向《大紀元》記者表示,7月19日被綁架當天,許那在家中和其他法輪功學員正在一起學習法輪功書籍,當時一共有14至15人被抓。許那目前被關押在北京東城看守所,絕食抗議。

2020年7月19日,許那在家中和其他法輪功學員正在一起學習法輪功書籍時被綁架。圖為李洪志先生著作的《轉法輪》。(新唐人)
梁小軍律師還在他的推特中寫道,「許那作為一個畫家、自由撰稿人,她的學識、她自身的悲慘遭遇和坎坷命運,帶給她一種深斂於內心的睿智、良知與勇氣。」
「殘酷環境之下,她淡泊名利。她本應有的名氣與影響,雖然被民間社會所低估,卻為官方所不敢輕視。每次會見她,於我,都是一種聆聽與學習的過程。」
許那對律師說,和她一起被捕的,大多是北京年輕的法輪功弟子,有些還不到20歲,所以她必須為他們戰鬥。
也許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站出來,為了良知、為了中國的明天而努力戰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