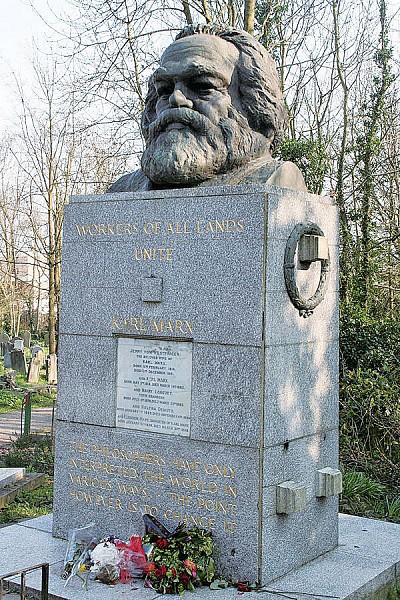劫後琴聲——中國第一代鋼琴家巫漪麗的故事

巫漪麗演奏的鋼琴曲《梁祝》的視頻在社交媒體爆紅,這個曾祖母級的鋼琴演奏家成了網路紅人。然而,有誰知道這是劫後倖存的琴聲呢?(視頻截圖)
對現在許多學鋼琴的音樂人來說,鋼琴帶給他們的是可以預測的榮譽和掌聲。 然而對於中國第一代鋼琴家巫漪麗來說,鋼琴帶給她一生的, 卻是從來意想不到的輝煌和磨難。
文 _ 夏墨竹
一位耄耋之年的羸弱老太太蹣跚走上臺,滿頭銀髮的她站在舞臺上,雙腳跟優雅地併攏,非常專業地給觀眾鞠了躬,便在鋼琴前坐定,背略佝僂。觀眾們等待著,她倒不急,停歇了10秒之後,才把手輕輕放在琴鍵上,那是乾枯的手指。然而她的指尖一落到黑白琴鍵上,瞬間流淌出的音樂,讓整場安靜下來。
老太太演奏的這段鋼琴曲《梁祝》的視頻最近在社交媒體爆紅,一夜之間,這個曾祖母級的鋼琴演奏家成了網路紅人。然而,有誰知道他們所聽到的是劫後倖存的琴聲呢?
她已經在中國舞臺上足足消失了50年,半生默默無聞。然而在上世紀50、60年代,「巫漪麗」這個名字在中國的音樂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對現在許多學鋼琴的音樂人來說,鋼琴帶給他們的是可以預測的榮譽和掌聲。然而對於中國第一代鋼琴家巫漪麗來說,鋼琴帶給她一生的,卻是從來意想不到的輝煌和磨難。在共產黨統治的陰影下,為了雙手能彈鋼琴,她把她的雙腳、她的家,都付之進去了。她的琴聲在半個世紀的喧囂後聽來,掩不住的格外蒼涼。
年少成名
巫漪麗1930年出生於上海知識分子家庭。她的祖父是興中會登記在冊的會員。外祖父李雲書,在江浙一帶是赫赫有名的巨商大賈,曾擔任上海商務總會會長,在辛亥革命期間曾資助過孫中山先生。巫漪麗的父親巫振英,早年留學美國,是著名建築師。母親李慧英也接受過西式教育。
巫漪麗自幼習琴,對鋼琴和古典音樂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學琴一年,她便奪得上海兒童音樂比賽鋼琴組第一名。八歲的巫漪麗「稀裡糊塗」贏得了大獎盃。那個銀獎盃很大,她抱不動,舅舅把她抱在領獎椅子上,一起舉起了獎盃。當年的上海《申報》也報導了這件事。

左圖:1939年獲上海兒童鋼琴比賽第一名。(資料圖片)
右圖:青年時代的巫漪麗。(資料圖片)
獲獎後,上海一些有名望的鋼琴老師主動到她家,希望免費教她。她舅舅把她帶到意大利籍著名音樂家梅百器(Maestro Mario Paci)面前。梅百器是上海交響樂團的前身——上海工部局樂隊創辦人,他既是著名的指揮家,又是音樂教育家,20世紀初曾在德國獲得李斯特鋼琴比賽首獎,也是李斯特的再傳弟子。
梅百器在聽完巫漪麗彈奏後,當場就答應收下她。他沒有兒童學生,不到10歲的巫漪麗是他第一個小弟子。
10年後,巫漪麗在上海蘭心大戲院與上海交響樂團首次合作演奏《貝多芬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全場轟動。巫漪麗一舉成名,成為上海灘樂壇上耀眼的新星,「最年輕的女鋼琴演奏家」封號不脛而走。那一年是1949年,巫漪麗19歲。
琴瑟和鳴
1954年,她離開上海交響樂團,調往北京中央樂團。一年後擔任中央樂團第一任鋼琴獨奏家。鋼琴,不僅給巫漪麗帶來了無限榮耀,也讓她結識了一生的摯愛、中央樂團第一任小提琴首席楊秉蓀。
小提琴演奏家楊秉蓀自幼是個孤兒,比她大一歲,湖北武漢人,極有音樂才華。
巫漪麗和楊秉蓀的婚姻,當時人人稱羨。夫妻組合的黃金搭擋,合作相當默契。兩人琴瑟相調,鸞鳳和鳴,一起合作過多首曲目,他倆同另外三人還合作演奏過舒伯特的A大調鋼琴五重奏《鱒魚》。
1962年,32歲的巫漪麗獲評國家一級鋼琴演奏家。在命運的最高音上,她聽到歡湧的琴音到了潮尖。然而黑暗剛硬的低音已經敲響,一步步放大,吞噬了這最華美的樂章。1966年,音樂戛然而止。
共產黨的政治迫害
在這之前,巫漪麗和楊秉蓀每天都是要練琴的,他們從未想到自己當寶貝的西洋樂器會被無產階級打翻在地,再踏上它們的大腳。然而,紅衛兵和造反派已經明令宣布:不准他們再拉琴、彈琴了。
他們偷偷地練琴,楊秉蓀把指法和運弓分開來練習,不讓他的琴發出聲音;巫漪麗也在無聲地練彈。琴是無聲的,音樂在他們心中。
當時中央樂團還是樣板團,在文革中,「樣板團」可是個響亮的名字,因為它們是文革「旗手」江青親自抓的典型,是江青進行文藝革命的「試驗田」。何蜀在〈從一個「樣板團」看一段大歷史〉一文中說,「在各地眾多文藝團體都因執行了十七年『文藝黑線』而遭到批判、清算甚至下放、撤銷、解散等打擊的時候,只有『樣板團』得天獨厚,被列入軍隊編制,人員都穿上了當時最時髦的軍裝,吃的是營養得到保證的『樣板伙食』,到各地演出都被當地『紅色政權』待若上賓……」

身處政治暴風眼的「樣板團」既是對外的櫥窗,又是對內的箭靶。樂師們的榮與辱、生與死卻常常只是一線之差。(AFP)
身處政治暴風眼的「樣板團」既是對外的櫥窗,又是對內的箭靶。雖然是全國唯一的樣板樂團,然而樂師們的榮與辱、生與死卻常常只是一線之差,一夕之間。
他倆經歷了「清理階級隊伍」和清查「五一六」運動,逼近的現實,異常冷酷,令人驚駭。小小一個中央樂團即有四人不堪誣陷迫害和酷刑逼供而自殺:曾任中央文革文藝組成員的陸公達跳樓自殺;原中央樂團黨委成員、樂隊隊長陳子信觸電加喝殺蟲藥自殺;曾任全國文藝界造反組織負責人的巴松管演奏員門春富用書包帶上吊自殺;樂團成員、低音大提琴畢業學員依宏明以鐵絲上吊自殺。
楊秉蓀沒能逃出去。這位曾留學匈牙利的首席小提琴手被打入「反革命小集團」,判刑十年,成為了階下囚。這回,他被迫和心愛的小提琴,一刀兩斷。
監獄可不管他是個首席小提琴手,把他分到幹重體力活的施工隊。楊秉蓀天天用拉小提琴的手搬水泥墩子,澆築水泥塊。因勞累,他患上腰間盤突出,苦不堪言。即便在獄中,楊秉蓀還是忍不住在心裡想像著琴的樣子,偷偷練習。
鎮壓精英的翻雲覆雨
丈夫突然被打成反黨集團的頭目判刑十年,對妻子巫漪麗來說猶如晴天霹靂。一下子成為反革命家屬的她,很難接受這樣的事實。她徹底嚇壞了。專制的低音咄咄逼人,猙獰可怕,令人窒息。她什麼也顧不得了。輾轉反側之後,她做出了一個改變她一生的決定,這是一個痛苦的決定。她找到軍宣隊開介紹信,再找法院申請離婚。這段婚姻結束得太倉促,他們還沒來得及要孩子。
獄中的楊秉蓀接到離婚通知書,二話沒說,就簽了字。兩個彼此相愛的人,自此各奔東西。楊秉蓀繼續坐牢,巫漪麗保住了她中央樂團獨奏演員的地位。然而她的「樣板」人生並沒有好轉。她被趕到小閣樓,有人張貼她的大字報,她的鄰居直接把番茄醬丟在她的門板上。
半夜兩點,她被突然喊醒,蒙著眼睛押走。被造反派毆打時,她哀求:「別打我的手,打我的腳吧!」從那以後,她的腳便留下了病根,到如今,脈管炎已經非常嚴重。巫漪麗和她的一些同事被送往北京郊區的幹校,繼續遭受迫害。在很多個護田看水的夜晚,她仰望星空,過去的日子又重新來過,心裡瞬間滿溢的音符,倉皇皇不知奔向何處。
那邊的楊秉蓀卻又成了紅人。彼時他在河北二監獄服刑。監獄的費獄長打算開展文娛活動,開個新年聯歡會。楊秉蓀為了表演節目,寫信給前妻巫漪麗,請她把自己的小提琴寄過來。因為兩人雖然分開了,可楊秉蓀人在監獄,東西沒法分。所有的東西,還放在他們當年的家裡,包括楊秉蓀那把珍愛的小提琴。
美籍華人作家張郎郎當時因組織地下文學沙龍「太陽縱隊」蒙冤入獄,和楊秉蓀關在一起,他後來記錄下當年楊秉蓀火爆河北二監獄的情形。
「當隊長聽說當年為買這把小提琴老楊花了多少錢,當時都傻了,獄部決定派專人到北京去取這把珍貴的小提琴。」
「二監獄的幾位隊長到底是公安戰線的老將,幾經周折,總算把這把珍貴小提琴全鬚全尾的帶回了石家莊,交給了老楊。也許你不知道,這把琴對老楊意味什麼。當費獄長隨隨便便地把這把小提琴遞給楊秉蓀的時候,老楊當時的雙手發顫,那臉上的表情無法描述。彷彿他捧過來不是一把提琴,而是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
1975年的新年,在六千多名男女重刑犯在場的新年聯歡會上,在層層密布的電網中間,反革命分子楊秉蓀平靜地站在那裡,他的一曲小提琴獨奏轟動了整個河北二監獄,連四面砲樓裡站崗的士兵和機槍手們都在聽。
「『楊秉蓀就在二監獄服刑!』的消息不脛而走,傳遍石家莊,甚至傳遍河北省。在第二年的新年晚會時,來了許多『貴賓』。他們都是為了聽老楊的琴聲而屈尊參加我們犯人的晚會的,其中,有河北省駐軍文工團的演員、有支左軍隊的首長和省革委會主管公安或文化的官員以及他們的家屬。」
此後,楊秉蓀每個星期都有機會坐著隊長的吉普車,出監一兩次。那是要他去給某個領導的孩子上小提琴課。
他和他小提琴的戲劇性重逢,真是讓人哭笑不得。

1979年3月19日,楊秉蓀(中)與波士頓交響樂團首席小提琴手約瑟夫.西爾弗斯坦(右)等在演奏休息時交談。(新紀元合成圖)
覆水難收
1977年,楊秉蓀被釋放出獄後重回中央樂團。他有了新的家庭,有了孩子。1991年,他和全家定居美國休士頓。
80年代,年過半百的巫漪麗,獨自一人離開中國,赴美深造。此後,她常常一個人乘坐飛機行走世界。1993年,她定居新加坡,租一個單間,和房東一家人同住一個屋簷下,以教琴為生。除了教學,巫漪麗每天仍舊堅持練琴兩三小時。她痛惜的說:「我感覺到我已經失掉了很多練琴的機會,所以我就不敢疏忽。」

2008年,78歲高齡的巫漪麗出版了首張個人專輯《一代大師1》,在業界引起了強烈反響。
年少成名,半生漂泊的她在78歲時,出版了首張個人專輯。2013年,83歲的她出版了第二張個人專輯,其中收錄了當年她和楊秉蓀等五人的鋼琴五重奏——舒伯特的A大調鋼琴五重奏《鱒魚》。她特意託朋友從新加坡給身在美國的前夫楊秉蓀帶去。
音樂還在悠然流轉,然而當年天造地設的那對才子佳人的故事早已流散,湮沒在黨媒宣傳的輕薄言笑中了。
2017年5月,巫漪麗榮獲世界傑出華人藝術家大獎。也是在這個月,楊秉蓀在美國休斯頓病逝,享年88歲。他的妻子和女兒隨侍在側。
在巫漪麗的生平介紹中,有意無意,那最不可思議的20年(文革前後),是一筆略過,幾乎是空白的。對於年事已高的她,再多的榮譽,再多的讚美,也不應,也不能塗抹這20年的驚擾。琴聲不能再被強權利用,成為給它們臉上貼金的金粉。
20年,豈是筆尖能輕易滑過的?任憑抽去,但琴聲帶不走。那是她的20年,都在那裡,她生命的分分秒秒都在那裡,那是她最頂端上的跌落,是生命最美滿時的殘缺。20年的樂章殘段,是一步一步的求生掙扎,是生生的分離和決絕。淚水裡有血,只是不與人說罷了。
深沉的回聲,充滿剛性的敲擊,她生命的重音在那裡。無力遺忘。
那被強權奪去的琴聲,最終會回來,化成不息的聲聲追問和永不忘記的見證。◇
|
|